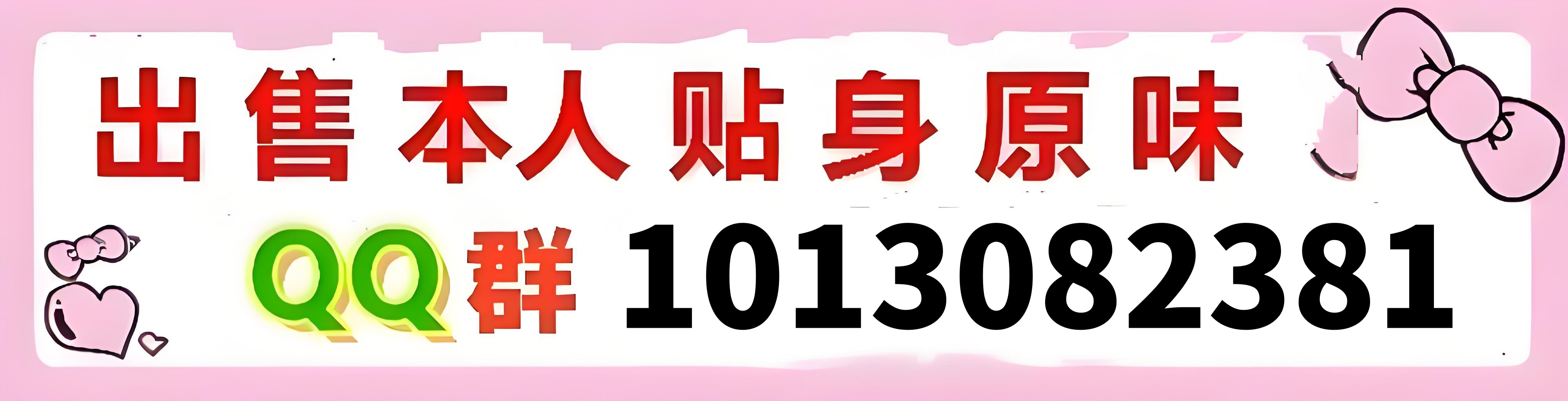
原味出售QQ群 1013082381 永久网址 www.yuanweibuluo.com 原味部落全拼
优秀的谍战戏常常有一种低调的理想主义。引人入胜不仅因为强情节高智商烧脑悬疑,而且因为相比于一些狂轰滥炸的战争戏和口号语,它更可能呈现出干练、隐忍、凝重的质感,同时更接现代人心理的地气。剧情往往在怀疑与被怀疑中推进,然而怀疑背后的承重墙是信任,对组织和事业的信任。如果这份信任可以支撑人身涉险境临危不惧、面对怀疑酷刑或诱惑都坚定不移,还要经受同志的误解排查,那应该就是信仰了。谍战戏的结局不会让你失望,有信仰的人绝不会蒙冤受屈。任何年代任何社会,人们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怀疑,总会羡慕那些内心笃定的人,不是总会得到一个美好结局。因此优秀的谍战故事自有其生生不息的魅力。
《地下地上之大陆小岛》
谍战戏《地下地上之大陆小岛》应属此类。该剧由凤凰传奇影业出品,石钟山编剧,张汉杰执导,胡军、柯蓝、冯恩鹤等主演;于9月7日登陆天津卫视黄金档,9月16日起河北卫视开始1.5轮跟播。这是首部涉及台湾VS大陆的谍战戏,讲述重庆解放前后隐蔽战线上的敌我斗争,围绕一份足以摧毁重庆城的“天下一号”爆炸计划,秦天亮(胡军饰)在重庆、汪兰(柯蓝饰)潜伏在小岛,凭借特殊身份和同志们的帮助与敌人展开较量。故事逻辑缜密,人物饱满,结构设计用心,正如剧中对“天下一号”爆炸设计的描述,“楼中有塔、塔中有楼、楼楼塔塔、塔塔楼楼,九九八十一环、环环相扣、扣扣相连。”

凤凰传奇影业投资制作过《新萍踪侠影》、《新白发魔女传》、《胜利者》、《一个鬼子都不留》、《我的抗战》、《上海滩生死较量》等多部精品佳作,屡创收视高点,《大陆小岛》是其新作。石钟山既是原小说作者,也是编剧,同时是制片人。八十年代至今,作为作家的石钟山一直保持创作、相当高产,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《军歌嘹亮》等作品在当代军旅题材谱系中都占有重要位置。2008年成立的石钟山影视文学工作室,不仅做剧本,而且更多地参与到制片中。深得主流认可的同时,石钟山视野并不拘于主流,对电视剧行业、电视台播出机制等均有独到的宏观见解。近日,独舌记者就《大陆小岛》采访了他。
展开全文
(1)勇闯台海谍战的新领地
独舌:谈谈《大陆小岛》这部剧,是根据您之前的小说改编的?
石钟山:《大陆小岛》小说是2011年出的,当时就考虑改编成电视剧。这个题材改编难度很大,限制很多。尤其涉及到国共斗争、地下党内部纪律;而且很多戏都是在解放后,国民党要反攻大陆,派特务进行很多活动。讲台海谍战,可以说是开创性的,审查也更严格。我们尝试看可不可以做,其实“大陆小岛”的小岛,在电视剧里虽然设计成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一座无名小岛,但它显然是有象征意义的,改编时把这个地点模糊化了。这个剧在上海、南京、重庆等地面频道播的时候反响很好,收视率都在年度前三,获了一些奖项。作为一部谍战戏,首先要烧脑,编剧设扣解扣、设计桥段要很讲究,不能让观众一看自己都能解扣,那就幼稚了。有些戏走的是情节,有些戏走的是人物,《大陆小岛》是情节和人物融合在一起,既重视情节,也重视人物塑造。
独舌:具体说说如何做到情节与人物并重?
石钟山:主人公秦天亮是一个“双面间谍”,他是坚定不移的革命者,但他要瞒住敌人,让敌人相信他是自己人,毕竟他的妻儿在小岛上被扣作人质,而且他的工作也需要这个身份,跟潜伏特务保持一定的联系,才能最终粉碎他们的计划。同时我方内部又有敌人的眼线,所以他在我方也不能完全暴露自己。既要向敌人隐瞒,又要向自己的同志隐瞒,是一个多方为难的状态。这样一个特定戏剧情境,对情节和人物塑造都是有利的。围绕秦天亮,他周围的一些人,包括同志和以前共事的特务,都可以得到一定刻画。我觉得一部类型剧里如果没有一个能立起来、让人印象特别深的人物,最多也只能成功一半。
独舌:戏里不时会出现一些内心旁白?
石钟山:这是一个辅助手段,这些地下工作者深入敌后,不能露出蛛丝马迹,想事情的时候无法跟人交流,只能靠旁白来表现。电视剧这种艺术形式也有它力所不及的地方;小说在这方面就很自在,想来一段心理活动就来一段。所以包括今年《平凡的世界》、前两年的《与狼共舞》,都用这种文学性的手段来辅助表达内心世界,让人物形象更丰厚复杂。
独舌:会特别考虑控制节奏吗?

石钟山:当然要考虑,写剧本要考虑,写小说也要考虑节奏。没有节奏就没有张弛,也就没有韵律。没有韵律的东西一定是枯燥无味没意思的。但是现在一说节奏,好像就是要快,其实不对,应该有张有弛。还有一些所谓的好莱坞模式在四处流传,比方说3分钟一个小包袱,5分钟一个大包袱,15分钟毙掉一个大Boss……类似这种,也对也不对。是有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总结,但首先每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不一样,观众欣赏习惯不一样;而且每个类型的戏也都不一样,都按一个模式做,所有的戏都成一个类型了。像很多人推崇的英剧、美剧,人家都不是按照一个路子做的。我们熟悉的英剧、美剧还都是他们比较有名的类型剧,其实他们有些肥皂剧也挺有意思,有人物、有情节,很日常的情境也能拍出丰富的感觉。做剧本,技巧并不是第一位的,人物塑造是第一位的。
(2)电视剧类型重复是资源浪费
独舌:为什么中国电视剧类型同质化比较严重?
石钟山:并不是中国的创作者没有想象力,而是一方面有很多审查上的限制,同时电视台的机制存在很大问题。电视台购片部门少数几个人按照他们的工作惯性和偏好做选择,再就是看什么播得火要什么,找同类的片子。没有引领,只是向市场妥协。包括现在的很多雷剧、神剧,很多小电视台都鼓励做抗战戏,说你们投入又不大,收视又保险,来多少我要多少。很多刚入门的小公司,拍战争戏起家,好像找到了一个成功的法宝,于是“手撕鬼子”这样荒诞不经的桥段泛滥,把严肃残酷的战争都娱乐化了。我们当然需要娱乐,但不要拿历史娱乐,让年轻人误以为抗战打得非常轻松;很多没有受过文艺方面训练的人会把电视剧当真的。要娱乐最好在虚构背景里讲故事,或者做动漫、游戏;如果涉及到历史,我觉得态度应该慎重。
独舌:电视台常常因为担心收视率而拒绝某些类型的剧吗?
石钟山:电视台看重收视率,因为直接关系到广告,广告是衣食父母。为什么英剧美剧好看,一个原因是播出模式和盈利方式跟我们不一样,我们电视台主要就靠广告收益。假如经济不景气,广告收益下降,就没钱收购电视剧,制片方也就没法做了。这个模式非常落后,亟待改变。其实我们电视剧的市场非常大,但是这么单调,两三个类型反复说来说去,重复劳动,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。有时候我们想做一个剧,可能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想法跟电视台充分沟通,他们就说这个收视率没保障,不要。一盆冷水浇下来,那能做什么呢,只好做生活戏,这个算比较保险。
《地下地上》
独舌:写现代生活戏会面临什么问题?
石钟山:写现实生活、家长里短,韩剧也有很多,但是观众可以允许韩剧娓娓道来,国产剧不行。因为韩剧它的表演方式、拍摄手法等等整体上稍稍还有一个陌生感,而且小细节往往处理得很好,我们观众能接受它剧情进展慢。但国内的生活戏被要求一定要强情节才好看,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,也不能太做细节的东西,会影响剧情推进。现实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戏剧冲突和故事桥段,那就制造桥段,让它激烈。于是人与人之间都是有矛盾的,老在吵架。媳妇、婆婆、小姑不和,夫妻离婚、出轨、复婚……总是一团乱麻、鸡犬不宁。这其实呈现的是人性恶。我有朋友出国,带这类片子给外国朋友看,他们看了说,你们中国人的家庭关系怎么这么可怕。造成这样的印象。
独舌:您有写过这样的戏么?
石钟山:没有,我主要写军旅题材和年代戏,比如知青下乡这样横跨十几、二十年的年代戏,还有《地下地上》《大陆小岛》这样的谍战戏。
(3)审查需要真正的专业人士
独舌:动笔写一部作品之前会先想审查的问题么?
石钟山:任何国度里的作家写作都不可能没有约束,政治性的约束、宗教性的约束、民族情绪的约束等等;不可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。我写小说也会考量,这个作品出来读者会怎么看,会形成怎样的社会影响,写军旅题材会考虑到我作为军人如何表现这个群体。出版也有审查,但跟影视相比要宽泛一些。影视的受众面和影响力更大,审查也更严。
独舌:审查现在是在放松还是在收紧?
石钟山:现在审查忽紧忽松,大家都在说,放开可能会出状况,紧了可能电视剧就要死掉。网剧以前是自己审查,现在它的影响慢慢变大,相关部门就会去规范它。但是我们没有一套完善合理的审查法律机制,是靠人在理解。设定的条条框框在大方向上没问题,但人的理解不同,就会造成很多问题。审查需要真正的专业人士,靠行政人员和老同志发挥余热是有局限的。
独舌:像《大陆小岛》这样的谍战戏会面对哪些限制?
石钟山:一般情况下,写正面人物要避免暴露他人格上的缺陷,写敌人可以写他的凶残狡诈,但避免塑造他人性善的一面。坏人脸谱化了,好人也脸谱化了,其实我们的文艺对英雄的表现还没有完全脱离“高大全”的式样。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之所以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欢,其实就是因为石光荣这个人物跟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有点不一样,那个戏往前走了一点,不仅写他光荣的一面,也写了他一些缺点,反而让这个人物更可爱了。
独舌:您的履历里好像有在北京广电局工作的经历?
石钟山:对,在那儿呆了三年,后来还是觉得搞创作更自在一点。
独舌:当时在局里负责什么工作,对您后来做编剧、制片人有什么影响?
石钟山:当时我们影视艺术处管立项、发许可证、评奖等等。我1997年去那儿工作,天天看别人的剧本,慢慢自己也尝试写。1999年写了一个剧《光荣街10号》,当时在中央一套播的,写离退休老干部的家庭生活。这段工作经历对后来肯定有影响,毕竟站得比较高过,对上级政策的把握、电视台的需求这些比一般人了解得多一点。之前我一直是写小说,从那时真正入行做编剧。
《光荣街10号》
(4)作家当编剧强在人物塑造
独舌:写小说的作家做编剧,会有什么特别的优势?
石钟山:我觉得作家当编剧,跟职业编剧相比最大的优势就在人物塑造上。如果一个编剧非常着迷于桥段设计和编织,可能就会让人物成为情节链条上的一枚棋子。这样出来的剧很类型化,人物性格雷同化,谁演都行,谁拍都行,是快餐式的东西。刚刚进入这个行当的时候,别人采访我,问编剧和作家这两个身份的问题,我说只是分工不同,性质是一样的,都是讲故事的人,都使用语言文字,万变不离其宗;但这么多年下来,感觉我们多数编剧在文学功底、人文涵养上跟作家相比还是有差距,可能跟所受的教育有关系,没有特别突出这方面。现在业内功力深厚的大编剧文学素养都很好,像高满堂,我们认识二三十年了,彼此很熟悉,他开始就是边写小说边编剧的,后来虽然没在小说这一块出来,而是在编剧领域发展出来,但文学功底是有的。他亲手操刀的剧本,人物饱满程度、人性挖掘力度跟一般编剧肯定不一样。包括刘和平的《北平无战事》也是,人物的魅力是第一位的,情节还在其次。不能本末倒置,让情节把人物给淹掉了。
《幸福像花儿一样》
独舌:您最开始接触影视,就是改编自己的小说吗?
石钟山:最早做改编是在1990年,改自己的小说《大风口》,那时候电视剧都是拍两三集、上中下,怎么做剧本我也不懂,就是那时候认识高满堂的,他是那个戏的责编。那会儿开始接触影视,但后面走得不成体系,断断续续的。做编剧主要是因为有小说被改出来跟自己想象十分不合的情况,落下一个情结,想自己动手。其实自己改编自己的小说有利有弊,好处是比较能保证原汁原味,坏处是很难跳脱出来。如果有一个改编者,既能原汁原味保留作品的精粹,又能给作品增色,那是最好的。一个好的改编者能从一部小说里发现很多东西,可能看到一句话,就能衍生出半集戏;而不是抛开小说或者大改特改。但这样珠联璧合的合作可遇不可求,很多时候改编既不能保证故事原味,又不能让它更加出彩。在这种情况下,自己改还是利大于弊。
独舌:如果跟导演一起改编剧本,会不会比较好?
石钟山:真正懂文学的导演并不多,而且往往已经做出来成为一线导演了,他们更希望拿到一个成熟剧本去拍,而不是费时费力打磨一个剧本。这些人最初还为找活儿而发愁的时候,会把自己当成半个编剧、策划,这样结果可以非常好。我跟一些优秀导演合作过,后来他们成名了,是有理由的,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他们比一般导演更懂剧本。我也遇到过没什么文化的导演,工作非常简单,任何一个剧组成员都可以做,要价还特高。我一直认为,如果一个导演不能在剧本基础上有他自己的贡献和建树,那就等于是摆设了。所以从制片人的角度讲,不管名气大小,只要能对创作有贡献,我觉得就是好导演。他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前期,而不只是在拍摄现场。
独舌:编剧做制片人,对创作者个人和行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吗?
石钟山:如果编剧或导演能对政策和市场有一个了解和把握,做制片会比一般的管理者更优秀。制片人是全方位的,什么都要懂一些,但最核心的还是剧本。如果故事不行,或者说IP不行,花多少钱都救不了;种子不行,结果不会好。从创作者的角度,把作品交给一个制片人,假如他对你的作品不理解,投资比例分配不合理,演员选择不对,呈现出来的效果不好,是很感痛心的。所以制片人懂剧本很重要。有些制片方只认贵的导演、明星,以为请到他们剧就没问题了;有些是被逼无奈,也不想花那么多钱请明星,但电视台拉广告需要,助长了演员价格越来越高,制作成本也越来越高。有些也不管这个演员跟这个人物是不是特别契合,违反艺术规律也得请;他对于创作者来说是可以被取代的,可以被很多演员取代,但对商业各方面来说又是无法被取代的。
独舌:说到IP,今年很多影视公司抢囤网络小说IP,您有关注网络小说么?未来会不会做网剧?
石钟山:合适的情况下会去做,但估计不会做《盗墓笔记》那类题材,可能还是偏传统的,网络对内容的需求是方方面面的。现在网剧发展还处在摸索阶段,《盗墓笔记》制作得很不专业,粉丝边骂边看,如果稍稍专业一点,好多问题是可以避免的。我平时看网剧不多,大家议论很厉害的时候去看一看,觉得看剧还是得多挑优秀的作品看,保护自己的品位和眼光。网络小说也是偶尔看看那些特别受关注的,我觉得网络上很容易看到冒芽的好点子,但比较难见精品。网络写手的写作往往缺乏节制,更新到后面就机械化了;而且大部分网络写手的文学功底并没有很深。IP这个东西不像黄金能保值,囤积起来今天不用明天用;一个故事行不行,内行人当时就能看出来,抢购一堆囤在那里,还是因为区分不清什么是好的。

【文/掌花案】
End
【影视独舌】
由资深媒体人、影视产业研究者李星文主编,提供深度的影视评论和产业报道。追求高冷、独立、有料,助大家涨姿势、补营养、览热点。涵盖微信公号,微博,博客,网站,今日头条,百度百家,新浪、网易、腾讯、搜狐自媒体等10大平台。



